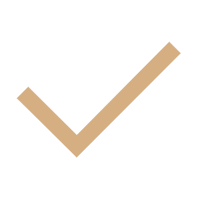第156章 尿
更新时间:2025-03-29 05:32:15
字数:2017
暴民见鹤顶红两人竟遁逃而去,声势又更壮多一些,彷佛他们不是农民,而是士兵,铁打的士兵。冲来之势当然又更加大了。
我见势头不对,立即转身就跑。可惜走了几步,胸口的伤口又再发疼,每走一步都撕心裂肺的痛,脚步自然不灵活,没走几步,就倒在路边了。
眼见暴民两三步就涌上来,有如大江潮水淘淘不绝,我只吓得看见了幻象,便是小时候睡觉时母亲抱着我去厕所,我却早一步进行发射程序,于是乎“一裤隔天涯”,现在想起,裤子竟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温热感……
暴民早已走到我身在之处,而且不断越前而行,彷佛看不见我,也碰不到我,只不断往前跑,不断叫嚣着。我看着他们,就似看着一只只掠空而过的燕子,轻轻巧巧的;又似袭来的战机,浩浩荡荡的。
待我意识回复清醒,他们早就不见人影,只闻远处还有声音。我既惊又奇,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只觉心脏跳动得快要从胸口的伤口奔出来。
忽然之间,背后又传来一声:“别作声,快跟我来。”此人虽叫我不作声,我却不禁低呼了一声。没办法,谁叫我忽然听到林杰的声音!
创作不易,感谢您支持正版阅读,维护作家权益
本章为VIP章节,需要订阅后才能阅读
订阅全部(共260章)
2345 北币
订阅本章
10 北币
本次订阅将消耗{{subPrice}}北币
当前余额为:{{balance}} 北币
余额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