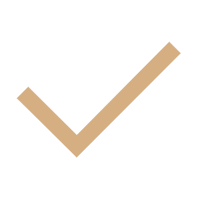做那种事真有些不可思议。有的人含辛茹苦,每每总是事与愿违,有的人却信手拈来一般,只消轻轻一碰就有了。花是这样,风吹过来,这朵花轻轻搭在那朵花上,便什么都有了。秋风之下,凋零的花瓣下那颗结实饱满的花骨朵就是它的后人了。草也是这样,草穗上沉甸甸的草籽,甚至人都不知它是怎么长出的。秋风一吹,纷扬的草籽如喧闹的孩童哗地跑向四处,落在哪儿就在哪儿长成新苗。松、杉、楠、栲,全是这样。它们耸立着高高的身子,躲在云中雾里成亲。只有竹子不是这样。竹子仿佛很害羞,有点儿象人。
它们总是躲藏在地下做成亲的事情,当一柱柱尖笋蹿出地面时,人才晓得它们得子了。偶尔有些竹鞭也会急不可耐地蹿出地面,它们就象村街上那些东探西望的山外客一样,想找处寻欢的地方打宿。兽分雄雌,树有公母,人为男女,化羽老道说世间万物只有阴阳二性。但山呢?谁也不知道什么山是公的,什么山是母的。它们也许全是公的,或者它们全是母的。谁也没见过它们成亲的事情。
它们没有脚,不会走靠在一起,相互依偎。它们没有嘴巴,不会发出相互倾慕的亲呢之声。它们拖着长长的身躯,终年默默地卧在那儿。它们是孤寂的。它们在酷暑中显得烦躁,在风雨中透出冷酷,在晨昏转换间显得固执而冷漠。山,大概是母的。天,才是公的呢!不管白日,还是夜晚,天空男子汉似地敞露着广阔的胸脯。
白天它用炽热的阳光拥抱大山,最阴湿的山涧都会散发出骄阳的暑气。夜晚它默默注视着大山,星星是它的眼睛。它的目光坚定,自信,不卑不亢,含情脉脉而专注耐心。只有男人才会有这温情而坚定的眼睛。山肯定是母的,只有在夜深人静之际才会体会到它母性的柔情。嘁嘁唧唧的虫鸣如摇篮曲,铮铮哗哗的泉鸣如絮语声声。
“四,不饿吗?天都黑了咯!”
天黑了吗?天黑了就好。所有的生命都是天黑诞生的。不错,天一黑下来,花猪母的叫声就更大了。它今晚就要生的。它那吭吭的叫声,与其说是痛苦,莫如说是幸福;与其说是呻吟,莫如说是歌唱。它将要生下来的不是一窝猪崽,而是给你带来的转机和喜运。彩彩跟着也要怀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