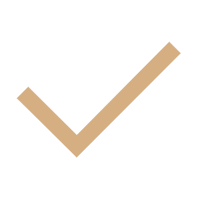第11章 欢闹
更新时间:2025-03-31 06:21:12
字数:5124
他迷迷糊糊进了里厅。他没料到客店的里厅又破又旧,黑沉沉的,房梁上结着蜘蛛网,弥漫着呛人的烟酒气,几十彪形大汉正聚在桌前赌钱,他们一面播着盏在碗重的骰子,—两又吵又笑。几个喝酒的枪手,满嘴喷着酒气,他们的舌头已经麻木了,却扯着公牛嗓子,一边用拳头擂着桌予,一边仰头齐声高吼,而门旁孤零零的那个红鼻头枪手,却呆呆地捧着酒碗,他一面嘟嘟嚷嚷说着什么,一面微笑着频频摇头。一阵阵放荡的笑声从那两间挂着布帘的门里传出。忽然,一个千嚎似的哭声响起。他四下巡望,发现发出哭嚎声的是一个千瘦干瘦的老头,抚着泪痕,神情恍偬。他也是个枪手吗?一群争食的狗在桌下的低吠,滚成一团。几个脸上抹着白粉的胖女人,扭着水桶般的爱身,在人群里摆来扭去,整个客店响着粗野的笑声。
把门的伙计喊过之后,厅里顿时寂静下来。那些惶惑、不屑、戏谑的目光全移到他身上了。
“莫睬他们!”傅天鹏倒象个常客,拽着他坦然坐下。
“那老头是谁?”
“麻叔。啃剩骨头的一条老狗了!去年在山里偷取人家地枪打着的山兽,被人家捉住,好一通惩治呢!今日到这里当然要为大家拿钱买酒!”
你不睬人家,人家却要睬你。那帮赌够了的枪手,哗啦啦推开椅子,笑嘻嘻地围上来了。刚才那个呆对酒碗,嘴里嘟嘟嚷嚷的红鼻头大汉一走过来就吼道:“喂,知道这里的规矩吗?”
创作不易,感谢您支持正版阅读,维护作家权益
本章为VIP章节,需要订阅后才能阅读
订阅全部(共28章)
635 北币
订阅本章
25 北币
本次订阅将消耗{{subPrice}}北币
当前余额为:{{balance}} 北币
余额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