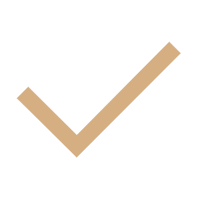第9章 选媳妇
更新时间:2025-03-31 06:21:12
字数:3639
哗啦,空咚——哗啦,空咚……水磨平静地转着,石臼平静地捣着。一阵阵风拂动着竹林,竹林发出一阵嘤嘤的声息。风停之后,一切静极了。他喘息半晌才扭过头看看彩婶,彩婶仍然一动不动,那双含笑的眼睛仍然静静地仰望着天空。刚才他伏在上头看时,彩婶也是这副神情,那双微笑的眼睛也是一动不动。他以为她在看他,但后来他渐渐发现彩婶的目光是漫散的。彩婶目光的焦点并非投聚在他脸上,而是投向他的身后。身后有什么?白云。蓝天。起伏的山峦。苍苍莽莽、莲蓬勃勃的森林。很久以后他才明白,那是一道投向未来的、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目光,那里面有责任和尊严,有期待和渴望……
哗啦,空咚——哗啦,空咚。
“汪汪汪……”
谁来了?他倏地坐起来了。彩彩笑道:“怕吗?我的狗不咬人!”离开工棚时,石臼仍然平静而耐心地一起一落,口哗啦,空咚
——哗啦,空咚……”只有那声音为他们送行。
村里人不知道两个做纸师傅何时离开工棚下山的。人们始终以为他们还住在山里。因为,夜深人静的晚上顺着风还能听听那阵石臼有节奏的捣磕声——空咚——哗啦,哗啦——空咚。有一天,石臼声突然停止了,从此再也不响了。人们上山一看,方知做纸师傅走了,纸棚倒塌了,篾帘撕碎了,满池的纸浆发出酸臭酸奥的气味。那根石口的轴柱已经断折,高高翘指着天空,臼窝空蓄着一泓雨水,已经蒙起一层苔藓……
创作不易,感谢您支持正版阅读,维护作家权益
本章为VIP章节,需要订阅后才能阅读
订阅全部(共28章)
635 北币
订阅本章
15 北币
本次订阅将消耗{{subPrice}}北币
当前余额为:{{balance}} 北币
余额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