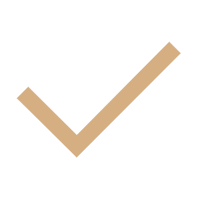老港农早瞅见他俩的险境了,瞅了个机会想开溜,被姑娘发现了,姑娘几下便追上了他,把他往地上一按,说:“哟,亲爱的,这是要往哪儿跑呀?你难道不爱我了?”
老港农连连摇头,说不了不了,再也不敢爱你了!其实他想错了,他如果说“爱,还是爱,你把我吃了吧,这样子咱们就能永远在一块”之类的肉麻话,说不定女孩儿一感动,还能放他一马,结果他一心急,押错宝了。
姑娘一听他说不爱,顿时怒了,没有用黑紫色的细针叮他,而是嗡嗡叫了几声,她声音停下时,就见老港农的脸上和脖子上诡异地冒起了肉泡,肉泡越冒越大,最后破裂了,从里面爬出千千万万只带翅膀的小蚂蚁,这些蚂蚁顺着他的脸爬到他身上,在他身上钻进钻出,很快把他啃成了一具白骨,片刻后,连白骨也啃没了。
“哼!你这老家伙,傻不拉唧的,还找那个什么先生摆阵,害得我三天两头生病,要不是看你钱多,早就把你喂我儿了!”姑娘收起翅膀,一扭一扭地走到我跟前,一指刚才老港农被啃干净的地方,说:“看见了?你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钱,跟他一样!”
我和瘸子发了横财,转眼又吃了大亏,成了穷光蛋,这一起一落,仿佛做了场梦。俩人失魂落魄地走到住处,摸摸兜,凑出三百块钱,找了个摊子吃东西,回想这段时间的遭遇,唏嘘不已。一瓶二锅头很快喝完了,俩人又开了一瓶,瘸子说:“唉,想着昨天咱们还是茅台五粮液,今天就成了二锅头,这真是鬼催的。”
我说:“本来那钱就来得虚,散得当然快,没了就没了,这有啥!我这肚子里还有一堆虫子呢,说不定啥时候就成了人家的蛋白质,你说什么还不比我强啊。”
瘸子说:“兄弟你看你这话,你的事就是我的事,别管了,咱们虽然现在没了钱,但咱们的名声还在,我们明天就去找黄维史,让他再给介绍个客户。”
我说:“去去去,你还敢去招摇撞骗?这下差点把命丢了,一点记性都不长?”
瘸子把头一梗:“那你说怎么办?你会干嘛?我会干嘛?我只会收废品!咱三个月上哪儿去弄600万?”
我语塞,只好端起酒,说:“喝喝喝,不想那么多了,今朝有酒今朝醉。”
这天,俩人喝了三瓶二锅头,摇摇晃晃的,居然忘了自己已经搬家,竟又走到了那个古村。他们原来住的小屋已经被拆了,剩一片破砖烂瓦,旁边搭了几个棚子,拆迁工人全住在棚子里。
二人靠着河边一棵树,不觉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,忽觉脸上凉丝丝的,有个软滑的东西在蠕动。我睁开眼,发现面前站着个身穿花大衣的胖子,胖子朝他一拱手,说:“二位师傅好,在下阿花,是江老板派来的,想请二位去公司坐坐。”
我心说这又是哪个老板的马仔,怎么稀奇古怪的?这时候瘸子说:“好好,这好说,不知你们老板找我们何事?”
阿花说:“这,我也不清楚,你们见了他问他自己吧,我只是个送信的。”
瘸子说:“好,带路,我们去会会那个江老板。”
恍惚中,二人随着阿花来到一处幽暗的大坑前,低头一看,有条台阶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坑内,由于太黑,看不到底。阿花走在前面,二人跟在后面,三人一块下了大坑。顺着一条扭曲的走廊一直走,走了很久,眼前豁然开朗,出现一个大厅,大厅内装饰得很有个性,不是中式,也不是西式,而是波斯式。——四面全是水晶,椅子是水晶的,桌子是水晶的,两边站的服务员身上穿的衣服都镶满了水晶,被天花板的水晶灯一照,整个一水晶宫。
这时候,大堂椅子上坐着的一个大个子说话了,话语间带着成功人士的腔调,他说:“二位好,你们就是林清子师徒吧?久仰久仰,在下江泥子,是这公司的老板,呵呵,请坐请坐。”
我和瘸子落座后,江泥子说:“唉,我大小就爱听老龙王的典故,最向往那个水晶宫,这不,现在咱们手头宽松了,就也试着弄了这么个地方,虽然比不上那老二货的宫殿,可着实也费了一番心思,二位感觉如何?”
我四下环顾一圈,连竖大拇指,说:“感觉棒极了!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!”
江泥子似乎不满足,又问:“就只是漂亮?”
瘸子听出他想让人奉承自己,便投其所好,说:“唉,其实我徒弟只是笨口拙舌,他的本意可不止漂亮这么简单,他是想说,这地方,啧啧,实在……实在……实在太漂亮了!”
我在旁想笑,心说你这瘸子怎么连夸人都不会夸,看我的。我接过话茬,说道:“这地方,啧啧,晶莹剔透又八面玲珑,处处透着后现代印象派风格,再加上蒙太奇手法一对比,更加衬托出非凡的意境,这只是宏观印象,再微观一下,水晶吊灯,看似普通,实则雕刻手法新颖独到,将中西美学毫无瑕疵地结合了,大厅的地板,啧啧,美而不华,光可鉴人,和天花板相映成趣,相得益彰,这这这,这地方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现!别说什么龙王的水晶宫了,恐怕玉皇老儿的瑶池殿都得甘拜下风。”
江泥子听得嘎嘎大笑,习惯性地伸手想去撸胡子,想来以前是有胡子的,但现在成了光下巴,只是空撸。得意完了,他打个响指,说:“来人啊,备酒,奏乐,舞起来!”
不大会儿,几个服务生摆上了一桌佳肴,一帮穿着性感的女孩儿排着队走进了大厅,笑着给三人鞠躬,然后跳起了类似探戈改编的舞。我仔细一打量,发现别的都好,就是乐队成员的模样一个比一个怪,有的穿着一身绿衣服,光着头,却留着半边胡子,胡子长得地方还不在唇边,而是脸颊上;有的大嘴歪着,叼了根雪茄,不见他嘴动,只见雪茄冒烟;有的倒立着,用脚弹琴。我虽然觉得怪,但也不敢问太多,他知道这些搞音乐的弄出的造型总是有说头的。
欢乐了一会儿,江泥子话锋一转,提起一件事。他说:“前段时间我们蛙经理不小心被二位杀了,二位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?”
瘸子一愣,就想让他别开玩笑,这玩笑不能乱开。谁知江泥子突然笑了,又说:“哈哈,其实没什么,我不是问罪的,我是听闻二位神通了得,想请二位帮个忙。”
我问:“帮什么忙?”
江泥子说:“唉,你别看我现在风光,其实背地里也愁得很啊。”他有什么愁呢?他和所有发家后的男人一样,都愁老婆命太长。江泥子把瘸子和我拉到内室,悄声道:“那母老虎,凶的很吶,你看。”说着,他撩起胳膊给二人看,他胳膊上赫然全是血痕,像是被什么抓的。他又撩起了大衣,露出腿,腿上和胳膊的情形一样,也是布满了血痕。我却注意到他大衣内只穿了条内裤,于是调侃说:“哟,江老板这造型好啊,儒雅中透着不羁,不羁中又透着霸气,敢问是哪个时装设计师给您设计的?”
江泥子一听,顿时有点窘迫,说道:“你看错了,我这是自由惯了,受不了裤子的约束。”
这时,瘸子说:“这件事我们不能答应啊,杀人可是重罪,我们不敢冒这个险。”
江泥子一拍脑门,恍然大悟道:“唉,你瞧我这记性,我忘了告诉你了,我根本不是人,我老婆更不是人。”
“不是人?”我和瘸子异口同声问。
江泥子点点头,说:“怎么,你们这么久都没看出来么?我是这河底的霸主,跟赑屃是亲戚,根本不是凡人啊,我那个老不死的女人是个螃蟹精,她比我道行高,我受气受了很多年,又不能奈何她,这才向二位求助。”
我一听,心想这都哪儿跟哪儿啊,瘸子却满口答应下来,让江泥子把那个螃蟹精的照片拿出来。江泥子摆摆手,说不用什么照片,你们看一眼准忘不了。说着,他胖手一挥,幻化出一片景象。景象中,一个比他更胖的,圆滚滚,扁搓搓的恶女人正躺在床上吐沫子,一面超大号的镜子射出一道阳光,正好照在她身上,她喂喂眯着一对鼓囔囔的眼睛,八条腿带着节奏来回晃,似乎还听着音乐。
“这不,就是这婆娘。”江泥子说。
我一看,顿时乐了,说这老婆好啊,一脸旺夫相,你怎忍心加害于她呢?江泥子一张脸拉得比驴都长,说:“你这老弟,莫要取笑本座,本座的苦你又不是不知道,那婆娘太凶了,瞅见刚才跳舞的妹子了么?唉……那些妹子虽然漂亮,可是我却只能看啊,你想想,大堆靓妹围着你,你却只能看,这是什么滋味?所以说老弟,你和你师傅就帮帮本座的忙吧!”
瘸子动心了,说道:“帮忙好说,只是不知江老板准备出什么价钱。”
江泥子自怀中掏出几颗枣大的彩钻,放到二人面前,说:“这是定金,事成之后我另有酬谢。你们做她的时候,只需从河的北岸找到一块带字的……”他刚说到这,众人忽觉天地一阵摇晃,有个身穿黑西装的小眼男人跑进来叫道:“老板,不好了,他们又往河里仍砖块了!”他话音刚落,我忽觉脑袋一疼,竟被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砸中了,若不是水的浮力减轻的石块的冲击,恐怕非给砸个洞不可。他伸手一揉,忽觉眼前一晃,身体像被什么力场猛地吸了一下似得,嗖地挪了地方。他睁开眼,发觉自己已经靠在河边的一棵树前,面前扔着一瓶酒和一地烟头,敢情是做了个梦。